昆仑山下的玉峰镇,盛产美玉,盗矿者猖獗。
年关将至,一个名叫蔡正龙的护矿员失踪,多日未有音讯。妻子林雨虹千里迢迢来寻,竟靠丈夫“托梦”找到了他的尸体……
格尔木的冬季,酷冷,干燥。赤红荒山的盘山道上行驶着一辆白色轿车,孤零零的,在山石间若隐若现。路上砂石遍布,车一直晃动,听声儿,快要散架的趋势,刘瑞宁很担忧车抛锚在路上。已是下午三点多钟,顺着前行的方向望去,能看到雪峰峰顶的曲线,在日光下尽显妖娆。车已开过昆仑大峡谷风口,导航上显示,再走个十几公里就到京拉线了。
副驾驶上坐一个面色干净的女人,约有三十来岁。女人失神地望着窗外,眼睛里带点儿阴郁,头随车的颠簸,微微晃动着。她叫林雨虹,从两千多公里外的山东来,来找她的丈夫蔡正龙。格尔木的玉峰镇有座玉矿山,蔡正龙是那里的护矿员,一周前突然失踪,断了音讯。护矿队的同事找了数天,才在山石罅隙里找到一件带血的衣物。可能属于失踪者,也可能不属于。矿山地理状况复杂,山石风化严重,如有不慎,人极有可能发生坠落。另外,常有顺偏僻山道入矿山盗采的不法分子,也不排除发生恶性事件的可能。
林雨虹来,已是第三天。前天,昨天,都在等警察消息。今天早上七点多钟,天还没亮,她便出现在了派出所,说自己昨晚做的一个梦。梦里,她丈夫让人捅了刀子,并被丢进黑漆漆类似山洞的地方。
“那地方好像在过火车,轰隆轰隆的。”林雨虹形容得真切,好似真的去过那地方。她认定是丈夫托梦给她。
女人因寻人心切,大概已经魔怔了。
看着林雨虹哭红的眼睛,民警们都不无同情。可失踪的状况如非特殊,很难立案进行大范围搜查。所长老乌也只能做做样子,黑槽牙一开合,便朝昨晚值班的刘瑞宁下了任务:“去吧,你陪她走一趟。开3056去。”
3056是辆民改警的破车,没标识,没备胎,属于机动工具,极度缺乏存在感。在玉峰镇派出所,同3056一样,刘瑞宁也属于最没存在的那个。没人瞧得上他,连他自己都瞧不上自己。当警察原非他本意,来玉峰镇更非主动选择。去年此时,他还是在校园里晃荡的大学生,前程未卜。他终是熬不住父母的劝说,去考了公,闹着玩一样通过体检,随即便被“发配”到了这儿。
刘瑞宁的老爹是根红苗正的党员干部,说一不二。只道,“去吧,是个锻炼。”
突破极限熬了半年,刘瑞宁心里就只剩一个念头:辞职,赶紧回西宁,或是考研,或是找个别的班儿上。
刘瑞宁忍着困意陪女人上了路,很后悔昨晚打了一夜的手机游戏。战战兢兢驶过一条倾斜的侧弯道,路终于开始变得平直起来,他的神经才终于稍稍松懈。
今天是腊月二十三,朋友圈里,好哥们已在聚会,每日“歌舞升平”,泡吧,打团战,嫉妒得他牙根痒痒。小一届的女友顺利保研,还等着他回去庆祝。但眼下,如果女人的丈夫一直找不到踪迹,所长老乌怕是会一直拿他去应付这种鬼差事了。
绵延不绝的昆仑山,如若要让一个人消失掉,不过就像老天释放掉的一个叹息罢了。自打和田玉的荣光消散之后,美丽的昆仑玉取而代之,石头客们自然是趋之若鹜。荒山野岭中,莫名消失的倒霉鬼并不在少数。
林雨虹一路沉闷,也没怎么说话,只是叫刘瑞宁一直开下去,遇到有铁路的地方,才叫停,然后下去,走一走,看一看。一路走走停停,差不多跑了有七八十公里。直到前方出现一座加油站,林雨虹才冷不丁开口,问到了哪里。好像突然活过来一样。
刘瑞宁看了看手机导航,说:“快到海沟了。”海沟属于夏牧区,但草原严重沙化,远远望去,到处是斑秃一样的沙棘和红柳分布。
女人点了点头。
刘瑞宁客气问:“咱还接着找吗?”
“嗯。”女人没有丁点儿犹豫。她捏着手套,手套里放着手机。天气太冷,手机总自动关机,她只好用体温捂着。
刘瑞宁看了看天色,说:“天有点儿晚了,要回到镇上,也得三四个点儿。”他最怕走夜间的山路,破车的性能也让他心里不停打小鼓。
林雨虹没有回应。
“晚上会到零下二三十度,冷得很。”他补充说。
“很冷吗?”
“这边温差很大,你来了两三天了,应该能感觉出来。”
“再去找找吧。要找不到,今天就算了……”女人拿起手套,挡在耳后听了听,“那边好像有点儿火车声。”
刘瑞宁放大导航地图看了看,前方的确有铁路线,他点了位置点,规划出行车距离,大概能有个七八公里。但他心里想的是,还不清楚前边的路况,找到那里,估计今晚上得露宿了。肚子忽然空起来,“咕咕”响了好几声。从出发到现在,还一口东西都没吃呢。女人也听到了,终于表现出点儿歉意,说:“加油站应该有小卖部,先去那里吃点儿吧。我请你。”
车开进了加油站,林雨虹先下车,去了小卖部。刘瑞宁等着加油,加完,才走了进去。女人已买好桶装泡面,售货员正在加开水。刘瑞宁又要了一颗卤蛋和一根香肠。店里有简易桌台,两人坐了下来,拢着泡面盒子暖起了手。店的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寻人启事,女人望到那里,目光停留一下。刘瑞宁注意到,寻人启事已是一两年前的,是个年轻的背包客。在昆仑山区域,这种类型的失踪人员并不少见。坐下不到两分钟,手机响了,是所长老乌打来电话。他捏着响铃的手机走到门外,但立刻被警觉的加油员提醒。他只能挂断,去更远的地方回拨了电话。
一接通,老乌便连珠炮一样问:“怎样?到哪儿了?有情况吗?”
“到海沟了。”
“真他妈的实诚!车快开报废了吧!位置定位,隔段儿给我发一次!山高路远,带点儿脑子。”老乌一通臭骂。
“错了,所长。”
“错你娘个蛋!说说,都去了哪里?”
“都是过火车的地方。看到了,就停下来,走一走。”
“这娘儿们还真把梦当真事了。和你聊了点儿啥没有?”
“没有,我们基本没咋说话。”
“就没觉得人精神有点儿毛病?”
“没有,挺正常的。”
“我看你就不正常,实诚得跟个二百五。天再晚点儿,你就给钉那儿,别往回折了,免得到时出点儿啥问题,我还得去找你俩!位置定位发过来吧,挂了!”电话粗暴挂断。
自入职以来,刘瑞宁还从来没看透过满嘴跑脏话的老乌,土匪一样。不单对他这样,对别人也这样。这人不知是怎么混上所长位置的。
发了定位,刘瑞宁才又回到小卖部,吃完泡面,载着女人继续上路。开了大约半小时,两人便看到一座横跨荒山的高架桥,桥墩粗壮高大,颇显巍峨,桥下是蜂窝形水泥坝,一层层,最终伸向山体隧道。有只鹞鹰在铁路上方盘旋,翩然消失在荒山顶上。西天处,雪山的轮廓在暮光修饰下显得更为清晰,闪耀。望着渐渐靠近的铁路桥,女人喃喃地说:“像在梦里看到过的一样。”
刘瑞宁想,也许老乌是对的,如果不是精神错乱,不会说这样的胡话。
车开到了桥墩下,女人又说:“前面也许会有个山洞。”
“你也没来过吧。”
“感觉像有。”
刘瑞宁暗自发笑,是有那么一种人,很容易把梦嫁接到现实状况上去。如果女人能用这种方式来缓解找人的焦虑,还是不去打击她为好。
“在哪里停,我听你的。”刘瑞宁放缓了车速。
车穿过桥洞,缓慢行驶了一段,到达一个小山包。女人说:“就在那里停一下吧。”刘瑞宁停了车。心想,无非还像此前那样,又是白费工夫。
“你去瞧吧,姐,我就不下去了。”
林雨虹没说什么,下了车,向着山包走去,边走边观察着。山包顶部形状古怪,在逆光下,像个腰身佝偻的人。石头上长满了杂乱的灌木,层层叠叠,虽都是干枯掉的,但仍然显得茂盛蓬乱。刘瑞宁以为她很快就会上车,谁知她徘徊了一阵,竟抓着灌木丛攀爬了上去。他不由担忧起来,于是也下了车,向山包走去。
“小心点儿啊。”刘瑞宁叮嘱。
林雨虹没回应,继续攀爬。攀爬了一阵,又横向寻找了一阵,终于在一个位置停下。女人呆望着,像真的发现了什么似的。刘瑞宁有些担心她失足,于是也爬了上去。林雨虹转头看向刘瑞宁,脸上带点儿忧虑,说:“也许就是这儿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刘瑞宁手上扎了不少沙棘刺,正懊恼地撕着。
“感觉像是。”林雨虹指了指脚下松动的石块还有倒伏的灌木丛,“这里可能有人爬上来过。”
“是羊踩过的吧。”刘瑞宁看到了羊粪。“附近属于牧区。”
“你来看,这里有个洞。”林雨虹颤颤巍巍扯着灌木丛的藤条。
刘瑞宁上前,看到灌木丛里藏着一个三尺见方的不规则山洞,从阳光能照到的斜面看,里面大概有个深邃弯曲的空间。
“这些干草是折断下来堵在这儿的。”林雨虹说。
刘瑞宁扒了扒,藤蔓果然是断的。丢了块石头下去,“咔啦啦”一阵响动,片刻之后,才传来轻微的回声。看来洞子是有些深度的。他探身看了看,潮冷的气息立刻扑出。洞边的碎石因踩踏导致松动,他一个趔趄,膝盖抵着尖锐的石头,狠狠地磕了一下。
“小心。”女人忙抻住了他的胳膊。
“没事,没事。”
“能看到啥吗?”女人紧张地问。
“天太暗了,看不到深处。”
此时,洞壁上阳光已完全消失。刘瑞宁顾不上疼痛,打亮随身携带的手电,朝洞里晃了晃。光晕照到一处石头凸起时,忽然有些紫红色反光。刘瑞宁一惊,因为只有血迹才会有那样的反光。
刘瑞宁把手电交给林雨虹,去折了一根相对较粗的藤条,又从棉服里撕出一团棉花,缠在了藤条顶端,然后攥紧了,伸入洞子。费了好大一会儿工夫,他才将柔软的藤条搭在那处尖锐的石头上。他晃动几下藤条,让棉花沾上那疑似血迹的东西,然后才一点点把藤条抽出来。女人把手电照在了棉花上,棉花上的红色东西带着冰碴儿。刘瑞宁闻了闻,一股血腥味儿。拿手指捏了捏,冰碴融化,红色的东西染在了指肚上。与此同时,刘瑞宁又从棉花上发现几丝浸有血污的毛发。林雨虹也看到了,身体顿时颤抖一下。
此时,日光已十分灰暗。天际处,传来几声鹞鹰尖利的鸣叫。
“不见得那么巧。”刘瑞宁安慰着女人,“也许有羊掉下去过。”
女人沉默得像一尊雕塑。她不能不联想到梦里的情形,联想到可能发生的可怕状况。
晚上十点钟,一具尸体从铁路桥的山洞里被抬了出来。经林雨虹辨认,尸体正是自己失踪的丈夫蔡正龙。
尸体头颈因坠落而严重扭曲,身体和头颅一百八十度大错位。腹部有两处刀伤,刀口很深,基本可以判定,人是被杀后抛尸。而山洞石头上的那处血迹,很可能是在抛尸坠落时所遗留。
老乌对这桩离奇的案子很恼火。林雨虹当然可以猜测丈夫遇害,但梦到被杀后抛尸山洞,如此精准的巧合,实在难以置信。格尔木的刑事侦查员也到了现场。老乌将这一状况说给了他们。众人分析,如果不是巧合,那极有可能说明女人非常清楚丈夫遇害的内情,或者至少清楚某些相关的线索。侦查员对林雨虹进行了询问,但她仍坚持托梦的说法,至于为什么能找到这里,她称,并不清楚,只是觉得和梦里的情景很像。
可能因为悲伤过度,加上陌生的人群,高原的大环境,还有丈夫惨死的事实,林雨虹一度休克。现场人来人往,一片骚乱,老乌派人带她去了铁路警务室休息。
待在现场的刘瑞宁冻得瑟瑟发抖,双脚不停地跺着。自从警以来,他还从来没出过命案现场。从小到大,他甚至连死人都没见过,更不要说是被杀的人。老乌还顾不上理会他,他正忙于和格尔木的侦查员商议侦查方向。如此恶性的抛尸案件,必须尽快做好布控工作。
铁路桥附近的道路口都拉起了警戒,着重围绕这一区域展开调查。但荒山野岭,方圆数十里都无人烟,无疑增加了调查难度。凌晨一点,刘瑞宁才随老乌回到铁路警务室。直到下车,老乌的黑眼珠才终于瞪住了他,说:“你陪那娘儿们找一路,她真没透露点儿啥?”
“没有。要有,之前和您汇报的时候也就说了。”
“她和你说了那地界跟梦里的很像?”
“她是这么说的。”
“还说感觉人在那儿?”
“是。”
“之前去别的铁路呢?说没说过这种话?”
“没有。一路上,我们都没怎么说过话。她只是叫我一直开,只要遇到过火车的地方,就下车看一看,找一找。那块离海沟加油站七八公里,本来打算不去了,她是听到了有火车声,才想着再去看看。”
“那她咋知道那里有个山洞?”
“她可能是看到了那块有攀爬过的痕迹,才想上去看看。”
“你小子别蒙事儿,那女的这么说也就罢了,你别是受了影响,也跟着这么说。”
“您要不信我也没办法。我觉得找到山洞,可能就是个巧合。”
“你小子想法太嫩,别把人想简单了。”
老乌点了支烟,思索着,推想林雨虹这女人来玉峰镇也有三四天了,说不定和某个知情人见过面,获取过关于丈夫遇害以及被抛尸的信息,为了引起警方的重视,才故意弄出个托梦的鬼话。可她那伤心的样子又并不像在说谎。
刘瑞宁最反感被说“嫩”,他拒绝再和老乌对话,缩了身体,进了警务室。两个值班民警正围着“小太阳”取暖,他也凑过去“借光”。大风吹得窗户呜呜作响,回想起尸体的惨状,他的牙齿竟禁不住打战。老乌也被冷空气逼进了室内。林雨虹在警务室隔间,来了名赤脚医生,正为她打着点滴。老乌瞄了一眼。过度询问也不合适,他只能等待女人状态好转。
早上七点多钟,民警大鹏带回一个名叫多吉旺堆的牧民。多吉旺堆就住在距离海沟铁路桥五公里的山洼子,天气好的时候,他总会把羊赶到铁路这边来,对这一带算比较熟悉。桥下有个山洞他知道,放羊的时候,羊羔子曾掉下去过。多吉旺堆身子挂着土灰,脸上也有,走到灯光下,像个阴阳人,样子可笑。膀大腰圆的大鹏身上也有土灰,脸上挂着血痕。
老乌没好气地问:“咋啦?”
“这家伙把铁路上的铁丝网拿家围羊圈了。”大鹏歪歪嘴,吐掉一口血水,“我训了他两句,他可能没听懂,上来怼我两下。”
多吉仍不驯服,气呼呼说:“我那里的灯泡坏了,黑得很。偷羊贼的嘛,我当是。”
同去的警务室民警解释说:“这个多吉是喝过酒的。”
“就是的嘛。这倒有个讲理的人。”多吉附和着,“没哪个黑天来我这里,偷羊的贼才来。”
“他知道点儿啥?”
警务室民警说:“他说天气冷,最近一个月没来过这边。”
“那他娘的带他来干啥?”
“他说最近丢了羊,要报案。还有就是弄铁丝网的事儿。”
“边上处理去吧,屁事一堆。”
多吉被带到一边去抄写学习《铁路安全保护条例》,眨巴着泛红的沙眼,一脸的无辜。
老乌把刘瑞宁叫到了身边,说:“你去,找那娘儿们聊一聊。天也亮了,人总应该清醒点儿了。”
林雨虹并不在警务室,刘瑞宁出去找了找,才在附近的土坡上看到她。太阳刚刚升起,天空蓝得出奇。隔了一夜,一切恍然如梦。刘瑞宁爬上土坡,看到女人脚下堆着一个小土堆,土堆上插着三根香烟,她以香烟代替香烛做着祭奠。
“不清楚桌上是谁的烟,我拿来用一下。”女人说。
“没事儿。”刘瑞宁找不到安慰的话,但似乎也不是他该做的事儿。
“在我们老家,这样死掉的话,人是进不了门的。”
“打算把人运回去吗?”
“也不好运,路这么远。公公婆婆年纪都大了,身体也不大好,能瞒一阵子是一阵子。缓些时候,就说是出了车祸,骨灰带回去就好。”
两人随意聊起了天。
虽是带着工作任务,但刘瑞宁并不想去刺探女人关于梦的说法,他更愿意相信亲近的人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。质疑,显得很不人道。如果女人不主动提,他是不会和她聊的,即便女人是受了某些线索的暗示,误打误撞找到尸体,他也不认为去“揭露”这事有任何积极的意义。
“姐,要是我们所长再问起梦的事儿,千万别觉着冒犯,毕竟是为了查案。”他还是提了。他可以不问,但老乌和格尔木的刑警肯定会问。
林雨虹沉默了一下,问:“你今年多大?”
“二十四。”
“才二十四,我大你一轮。”
刘瑞宁以为她会顺着这话说下去,但没有,聊天尴尬地戛然而止。那口气就像她根本不屑于刘瑞宁的同情。她把刘瑞宁当小孩看待。
两人下了土坡,回到警务室。叫多吉旺堆的牧民还在抄写条例。刘瑞宁凑了过去,看到纸上的字歪歪扭扭。多吉看刘瑞宁一眼,咕哝着嘴巴,骂了句“帕路沙”。刘瑞宁没听懂,但听出了骂人的意味。
刘瑞宁说:“不要骂人。”
多吉说:“没骂你,骂偷羊贼呢。我知道是谁,我得写材料告他。你会写吗?帮帮我。”
刘瑞宁没理会他。多吉没皮没脸地又骂了几句,他有些燥热,敞开皮大衣,撕了撕领口。刘瑞宁注意到,多吉内里穿一件迷彩服,衣服缺了半边领子,领子边耷拉着半截折断的拉锁。刘瑞宁走上前去观察了一下。此前在现场取证的时候,他曾注意到格尔木的侦查员从死者的毛衣袖口上提取过半截拉锁,拉锁让毛线给嵌住了。恰在这时,老乌和格尔木的侦查员走了进来。刘瑞宁忙向老乌做了汇报。老乌看向多吉的领口,马上走了过去,说:“老乡,外套脱了。”
多吉一愣,“干啥嘛。”
“脱!”
多吉一哆嗦,把皮大衣外套脱了。
“里面的也脱。”
“冷。”
“叫你脱。你就脱。”
多吉乖乖把迷彩服脱了。
多吉刚一脱下,老乌马上把衣服扯到手中,眼皮一挑,在多吉脸上转一下。多吉不明所以,瑟瑟缩缩,瞪着白眼球。
老乌转身向外走去。刘瑞宁也跟了出去。格尔木的侦查员已打开警车的后备箱,后备箱里放着现场提取的证物,其中也包括半截折断的拉锁头。老乌把拉锁头从证物袋里取出来,比在了多吉迷彩服的拉链上。在众人的见证下,拉链头的茬口和迷彩服的茬口惊人地合在了一起。
多吉也走了出去,大叫:“把衣服还我!”他完全没有看不清状况。
老乌盯向多吉,抖抖衣服,“衣服哪里来的?”
“捡的。”
“捡的?”
“就是捡的嘛。那天刮大风,刮羊圈里来的,我看还很好,洗了洗,就穿了。”
“你倒挺会捡。还有别的吗?”
“捡到的东西多啦,你叫我咋说?”
老乌一把把多吉的脏手拉过来,那手上布满了血口子。老乌吓唬他:“你杀了人了!”
多吉一下子跳起来,“谁杀人了?你胡咧咧!”多吉像是遭遇了羞辱,上来就要和老乌干架。老乌两耳刮子打下去,把人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多吉暂时被铐了起来。折断的拉锁头忽然变成了重要的物证。从那件迷彩服的破损程度看,像是遭遇过激烈的撕扯。迷彩服是很常见的劳保款式,死者本身的衣服外套并无缺失,因此,被丢弃的衣服很可能属于凶手。如果迷彩服属于凶手,那多吉旺堆便有了嫌疑。格尔木的侦查员都颇为兴奋,但老乌认为,二百五的脸上是藏不住秘密的,如果杀人的事儿和多吉有关,怎么也能看出点儿问题来。
不过,侦查员们还是将多吉旺堆和迷彩服外套一起给带走了。
老乌说:“看着吧,下午就得放他走。”
果然,多吉旺堆下午就被释放了。
未完待续......
更多精彩内容请移步微信公众号 “戏局onStage”
作者 | 阿虎 编辑 | 赛梨
原文链接:《来寻夫的女人,说梦到了丈夫的葬身地 | 喋血昆仑01》
本文图文版权均归属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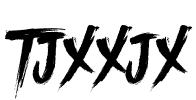

 1
1 3
3 4
4 7
7 8
8
